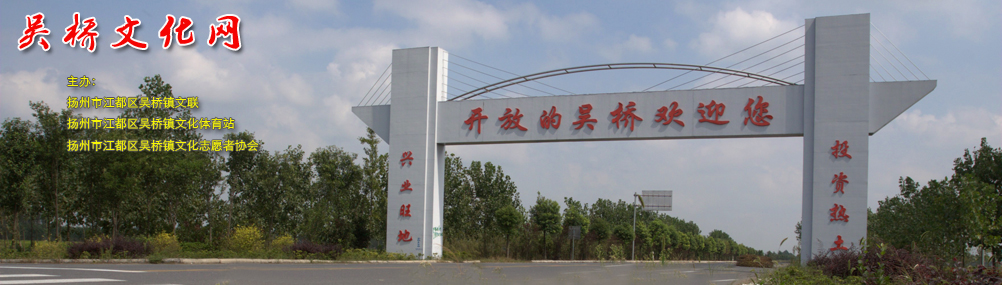|
白塔河是有名的,也是无名的。有名在它的历史,无名在它的现在,已变成一条“野河”。倘若时间可以并列,两条不同时期的白塔河出现在我面前,我宁可选择现在的这一条。它的美,在于它的“野”。
从江都328国道向东,到与安大路交会处折向南,白塔河就蜿蜒在路的两侧。这个季节虽然已立冬,但依然是晚秋。路边高的杨树、槐树、楝树、紫薇,矮的杂草,远处成熟的晚稻,都把上下天光染成秋色一片。
在通向吴桥蔬果园的乡路上,白塔河就横在眼前。这里没有车马喧嚣,不妨停下来,感觉到了画里。这画面很熟悉,前世见过似的。水静得纹丝不动,岸边的植物,生长得完全没有章法。丛生的芦苇有体格高大的,我记得小时候听人们叫它“刚竹”,属于男性;也有纤柔的,开着银白的花、状似小折扇,常常进入摄影家们的镜头。芦苇的下面是散散落落的狗尾巴草,已近枯黄。然后就是水边一片片的红蓼,这种植物,绿色的翅,穗状的花,也是极入画入诗的,所谓“红蓼渡头秋正雨”、“数枝红蓼醉清秋”。我很难表达对它的感情,它天生属于乡野,却又有着古代仕女一般的温婉摇曳。
其实白塔河的前世也是一条野河。在宋代《江都县图》及明《嘉靖惟扬志·图志》中,它的名字标着“白獭河”,原是一条南通长江,北接老通扬河的古河道。明朝永乐七年(1409)平江伯陈瑄执掌漕运后,主持疏浚开挖白獭河,把老通扬运河和长江沟通起来,成为江南漕船过江至扬州的一条运河。到了清代的《江都县志》上“白獭河”成了“白塔河”。奇巧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白塔河的河畔,真的出土了一座唐代的石塔,疑为寺庙之物,有人以此佐证唐代扬州白塔寺的寺址就在这里。
但我还是喜欢“白獭河”的名字,因为它充满了文学的想象与美丽。獭,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水獭猫”,我的感觉是一种比较神秘的动物,很难见到。但因为它的皮毛光泽耀眼华丽,被人追逐制作珍贵的裘皮而出名。古代的志怪小说中,水獭就像狐狸一样,常常幻化为美丽的女子与男子交往。而且因为她们生活在水中或水岸,女儿是水做的,她们是水的女儿,水便赋予了她们特殊的魅力。她们出场时,荷叶为衣,蕙草作带,“荷雨蒲风,小舟丽人”,极有诗情画意。
水獭的颜色是棕黑色或栗壳色,鲜有白色的。我猜想,如果有,那一定是得了白化病的水獭。在古代,人们或许缺乏动物学知识,一旦出现了百花现象,民间常视为祥瑞之兆 。顺着这样的思路,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年,这条野河里,有人看见了一只古灵精怪的白獭,人们奔走相告,方圆传遍了,从此这条河有了自己的名字。
我把这当做故事讲给蔬果园生态农庄的当家人方先生听时,他就笑,说什么东西到了你们文化人这儿,就是不一样了。我说你真是慧眼识福地。
彼时,我正站在他的度假村门口,与白塔河相距二三十米。放眼望去,一条小河蜿蜒北去。水边残荷待雨,蒲草摇风。河中一小屿,宛若微缩山村,天然图画。对岸平冈缓陂,白鹅们漫步徜徉。河的尽头便是一片青砖青瓦的院落。
这几年造园遍及城乡,土豪见过不少,但像这有天然野趣的还真不多。就离这不远处,有一处叫宗家院的地方,是清初名士宗元鼎故居地。我也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说白塔河这一代风光向来有野逸之气,宗元鼎离开扬州,便选择了在此隐居。而且据说是在东晋谢安的“芙蓉别墅”旧址上,盖了草堂,栽了梅花和柳树。到底是文人雅士,即便草堂,却起了风雅的名号,曰“芙蓉斋”、“新柳堂”、“梅西堂”,给那简陋的栖居以温暖,赋予这寂寥的人生以情趣。
方先生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梵高《向日葵》的底色上,有四个字:“此间向阳”,我说这四个字极好,怎会想起来的?他又笑了,说所有的植物中,他最喜欢向日葵,很单纯向上的样子。于是,搜了若干的向日葵的画,觉得还是梵高画中的向日葵,和自己心中想的比较契合。因为人生总是要有些追求的,到了这个年龄,更要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又说我们没文化,别见笑啊。
此时,我的眼前像是盛开了一大片的向日葵。他说他没文化,那是他的谦辞。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是和给白獭河起名字的人一样,真正的有文化。文学就是给这世界、这地方、这里的一切创造一个新的、真正的名称,如果第二个人跟着这样起,那才没有文化。能有这样特质的人,你能说他没文化吗?
他又说“此间向阳”,不是局限于他这里,而是泛指这一片地方。是的,我欣赏他这个泛指。事实上,我们向往乡村,向往乡村的天然野趣,向往那种恬淡怡然的生活,因为人生其实没有常住之世、常住之地、常住之家。乡村是我们与大自然最后一块联结地,只有在这里,或许我们才能在大自然变化中,找到显现的生之证明。它是我们的故乡。
人可以随时随地去行游,但故乡却很难随时随地发现,很难随时随地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