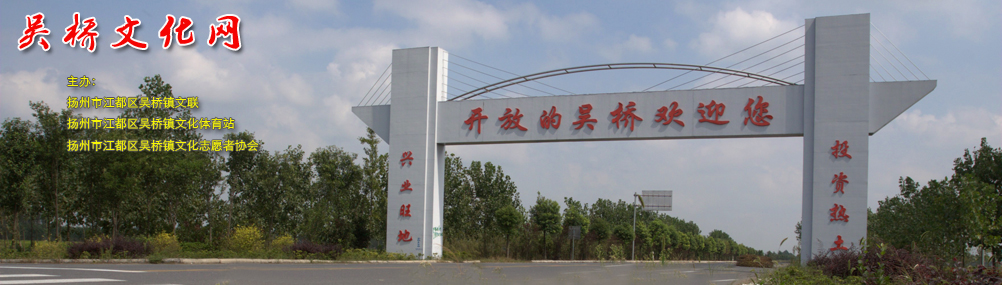天色渐渐暗了,帘儿半卷着。
一遍遍在菱花镜中,将那理了千百回的云鬓再细细去照;一遍遍在心里,将那要见的人儿反复地去想。两颊晕染的酡红,早已让玫瑰花的胭脂失色。
多么地静啊。窗外已听到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月儿该升起来了吧,只等它升上柳树梢头,就佩上香袋,穿过如昼的灯市……
这是一幕遥远而古典的元宵节情人约会的场面,这样的场面我们早已不复再见,连同女孩一低首的羞涩和酡红的粉面。
友人来闲坐,聊起现在人的大方,说她单位的一女孩喜欢一男孩,径直在众人面前,叠声说:“喜欢你,喜欢你,就喜欢你。”
这算什么?另一个说,现在男女,想说话,打电话;想见面,一个短信;千里之外,网上的视频早已粉碎了一切想像……
曾在三月清丽的风中对女学生做过“美丽的女孩,请保持一颗羞涩的心”的讲座,现在回想起来,羞的不是她们,而是我——想像她们在背后不屑的窃笑:整个一个老古董。
我到现在都羞于喊的“老公”,在那些不知情为何物的小女生传给小男生的字条里,早已顺畅如流行歌。
“远远的见你在夕阳的那端,打着一把细花阳伞,晚风将你的长发吹散,半掩着酡红的脸庞……”,青涩岁月的歌依稀在耳畔,但没有了时光不动难耐的渴盼,没有了兔子般喜悦的心跳,那一抹酡红已记不清在哪一个上元夜后慢慢地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