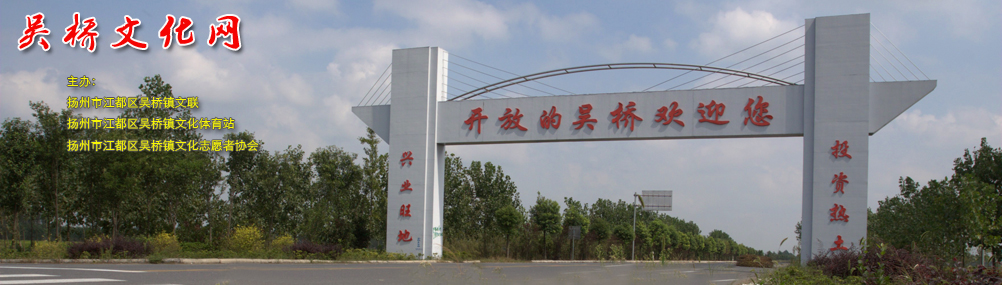门前的河塘,历来是桥西人吃用的水源。记得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初期的某年,成年累月不见一滴雨,河塘的水面越来越小,水体越来越绿,水里的红虫子越来越多。从河里担回家的水,妈妈虽然用细面筛罗将肉眼所见的虫子过滤掉,可腐臭味没有办法去除,也得吃,人们苦不堪言。
旱情在不断发展,河底终于干裂朝天,连一滴臭水也没有了。人们只能在河底掏大口井。渗出稀少的泥浆水,各家只能轮流舀几瓢回家,待沉淀后再用。
不用说,田里的禾苗已是一遍枯焦,树叶也纷纷脱落,几乎成为枯条。心急如焚的村民们,万般无奈,只得以土作龙,烧香、叩拜,乞求老天发慈悲,下一场透心雨。那时我们一群光着屁股泥猴般的小孩,也学着大人在干涸的河床边用泥巴作小龙。小龙头向上,仰望天空,尾巴向下,伸入干涸的河心,干枯的麻叶作龙鳞,两个田螺壳作眼睛,两根枯树枝作龙角。作好后,我们又学着大人,对着小龙叩拜、求雨。可老天对人们的一片苦心叩求不理不问,依旧我行我素:天空万里无云,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泥土发焦。
那年冬天,为了生活,我也随着奶奶,提着竹篮到自家地里揀枯菜伴食、充饥。来年春天,村里很多人家揭不开锅,不得不以树叶、野草充饥。我家也不例外,锅里少不了柳叶、榆钱、野草。即使以往的殷富人家,春荒来临时也不得不赶青(即提前吃未成熟的麦子)度日。
真是:叩天天不应,拜地地不灵。
农民苦日子,何时是尽头。
倏忽十多年过去了,1954年的春天,门前的河水,清净如镜,人们依旧在河里担水食用,涮洗衣服。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是:蜂蝶恋黄花,垂柳舞东风。
狡兔追绿野,祥鸟翱太空。
绿萍随波荡,清泉香茗浓。
灌园果菜旺,润心民轻松。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仲夏之际,一连多天的大风大雨,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门前的河水猛涨,漫过堤岸,大地一片汪洋,只有一个个孤独的坟头露在水面。
民房土墙,一面接一面轰然垮塌,留下孤独的屋架风雨中飘摇。有的墙体与屋架一起趴在水中。最严重的是我村的后庄,即所谓的七姓庄。那里外来户较多,他们的房屋比较简陋,墙体大都是土坯,经不起水泡。
疾风暴雨中,树的枝干,“咔嚓”折断声,此起彼伏。连根拔起的大树也不在少数。
野兔、老鼠、黄鼠狼等等惊恐地爬在草垛上,随风浪颠簸、飘流。长虫死死地缠上竹梢、树头,任狂风暴雨摔打。
那时我们家里和院里,水已漫到膝盖,我坐在床边上,脚就伸在水里划拉。
吃用水浑浊不堪,必须用明矾搅拌后沉淀。灶房里的柴草都潮湿了,找把干草引火都很困难。烧水做饭时,引火用的火柴,往往一盒用光了,柴草还没有点着。有时只能东家生火,西家沾光。
人民生活日用中的盐和火柴等,要到吴桥供销社去买,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门板和木盆,而且必须是会弄水的人才能撑着去。
半个多月的风风雨雨,终于停歇了,三天过后,田里的水基本退去。但经过长时间浸泡过的豆苗、玉米苗等等全部闷死,一经日晒,满目枯焦,惨不忍睹。
灾情发生后,人们没有退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抗灾自救。及时抢种荞麦、红豆等短期生长的作物以及各种蔬菜;没有种子,政府千方百计从外地调拨。房屋倒塌的人家,政府发放救济金,抢建房屋,保证过冬有窩。生活从紧安排,吃饭瓜菜代。
真是:官为民,民拥官。官民一体民心稳,新旧社会两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