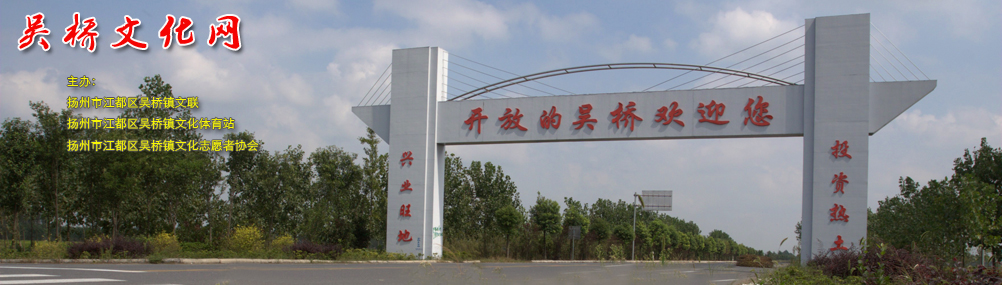金秋时节,到处是繁忙的丰收景象。黄灿灿的稻田一眼望不到头。我站在新修的农场路的路边,手扶着自行车龙头,欣喜地看着农场一致展开的多台收割机和停在路旁的几辆箱式运粮卡车。
收割机在茫茫的稻田里,像推光头似地收割一片又一片,吞食稻谷,排出碎渣(以利秸秆还田)。当机仓粮满之后,即开到地头,通过输送管,将仓里的稻谷自动输送到运粮卡车上。经过几台收割机轮番卸装后,装满的卡车便即开走。另一辆的空车又开过来接着装。周而复始,川流不息。
望着望着,往事幕幕涌上心头。
那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庄家收获靠两手,运输靠推车,劳动强度很大,而且产量很低。就秋收而言,成熟的粟子和黑豆,都是用手连根拔。
由于粟子秸秆硬,根系发达,扯(读ca)起来特费劲,我帮不上手。就坐在爸妈扯倒的粟杆子上,用专用刀脱粟穂(即将粟穗割下来)。边脱边前移,脱满一筐倒在麻袋里,又接着脱。
为了抢时间,我们总是吃在地头,休息在地头。奶奶负责在家里做饭,饭做好了,就用专用的饭篮一头装着饭菜和碗筷,一头挑着坐在筐里的幼小弟妹到地头吃妈妈奶。饭后我就躺在粟子秸秆上休息,芦柴蓬盖脸遮阳。
收好的几袋粟穗再由爸爸用木盘小车推回家碾压、脱粒。粟杆就地捆成捆,竖架在地里风吹、日晒,待干后再推回家堆成堆,留着生火做饭。
那时我们家的田里种的豆子都是黑豆。成熟时必须及时抢收,否则豆荚在太阳底下会自动爆裂,豆子散落在地里,收不起来。
扯豆也非常辛苦,秸杆不但硬而且扎手。为此,当启明星还未露脸、蟋蟀仍在旷野酣唱时,我就跟爸妈和奶奶一起下地了。铁叉柄稍上系着灯笼,插在地里照明。因为在夜露的作用下,此时的秸杆较软,豆荚也不炸。
扯豆时,爸爸一手一塘,两手左右开工,扯得很快。我虽然体单力薄,两手捧一塘跟着扯。一回爸爸扯豆时,将缠在豆秸上的一条土斑蛇抓在手里,吓得甩的老远,幸好没有被咬着。
天亮了,满田的豆秸都躺倒在地里,爸妈趁露水未干,又开始装车,将豆桔一车一车地推回家,铺在晒场上。下午爸爸妈妈还要顶着烈日用联枷敲打脱粒,我也跟着打。虽说此时已是秋天,但依然很热,即所谓的“火豆场”。
那个年代,农家一年忙到头,累死累活能保住一天三顿稀,夜晚有归宿就算不错了。真是:
农家无闲日,秋收人更忙。
腰酸筋骨疼,汤粥泥巴墙。
新中国建立后,农村虽然实行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劳动强度依旧不减,产量增幅不大。那时收获的粮食不但要交农业税粮,还要交定购粮,再去掉种子粮、饲料粮,剩下的粮食才作为口粮按大小人口分配,还是很紧张。
不久,高级社很快就过渡到以乡区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急切地走上了“一大二公”的道路,生产资料统统归公,生产劳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社员吃上了大锅饭,企图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其结果极大地挫伤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产量锐减,人民的吃饭更成问题!
之后虽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人民生活初步企稳,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降临了。
二十多年的折腾,人民的肚皮始终饱不起来,国家的经济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党和国家大胆地进行历史性转折,农村劳动力解放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种田的科技含量提高了,产量上去了。历来“种田完粮,天经地义”的神话被打破了,农民现在非但不交农业税,反而享受国家种田补贴,真是人间奇迹,世界奇闻!
实行二十多年的粮本和粮票以及一些购物券也逐渐取消了,人民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亦随之越来越高!
纵观现在,农村规模经营已是大势所趋,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经济将会一去不复返。
我常常和老伴说:“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片地,过去常年吃不饱,现
在多得不想吃;过去不想吃的粗粮,现在倒成了香饽饽;过去衣服补补再穿,现在光灿灿的衣服多得箱里压不下,成了多余物。”
老伴说,那不就是“现在政策对头,路子正了,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吗?!”
是的,现在正是如日中天,各行各业都在飞跃地发展!人民的生活还将越来越好!
有人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会变成这样好!这样的好日子真要感谢改革开放啊!感谢1978年的伟大转折!感谢党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和精准的顶层设计!”
想着想着,怀里突然响起了“特有的乐曲声”:“喂!快11点半了,你怎么还不回来!黄沙沟的吼表兄、五庄的大姐夫,还有你的几位老同学,他们都来看你啦!”
呀!我怎么就昏头啦!把这事儿都忘了!还愣着干什么,快骑车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