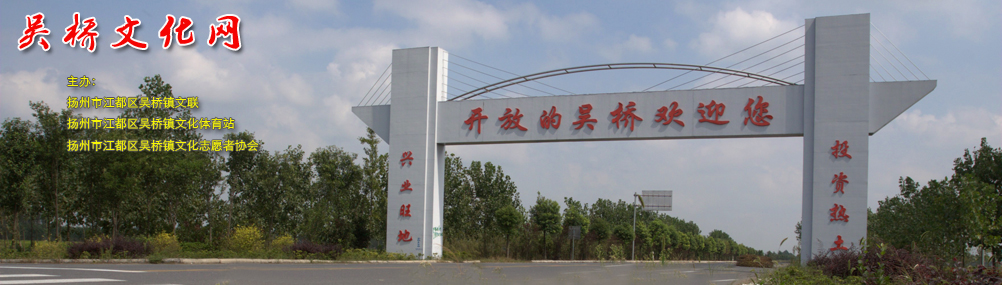那是在1961年的七八月份,刚跨入大学门。暑假期间,呆在家里也是呆着。不如找点事情做做。
田里种的花生、玉米刚成熟,老鼠就一粒一粒地偷走了,藏在它的地下“粮仓”里。地表也被它作撅得高一块低一块的。人们非常讨厌,可是一时又难于处理。
听说有人采取挖 陷阱消灭老鼠,简称挖老鼠。为此,爸爸就帮我在吴桥铁匠铺里,定打了一把小型洛阳铲,铲体呈弧形。回来再按上40公分的把柄,我就开始挖老鼠。
所谓挖老鼠,就是在确定老鼠的地下通道后,在通道的中途开始挖陷阱,阱壁呈园形、光滑,直径约8公分,深约30公分,陷阱挖好后,封好盖,不透光。并保证鼠路无阻碍,穿行顺畅。陷阱一连多个分布在地块的四周,范围不能太广,以便巡回检查。
一切就绪后,开始巡检。在揭开陷阱盖检查时,如陷阱中有老鼠,即捅死取出。揭开后的陷阱盖,无论有无老鼠,都要按原样盖好,等待后来的老鼠。
检查间隔时间以10分钟为宜。因为老鼠在地下快速穿行中掉入陷阱,一时懵懂,爬不上来。如相隔时间过长,老鼠会在陷阱里打洞逃跑。
经来回几次巡查,陷阱中若再不出现老鼠了,即说明老鼠的“家族”已被全歼,陷阱可以作废。
远近的生产队听说我们能挖老鼠,有效消灭它,便纷纷找上门,并以每只老鼠二两粮、五分钱的代价邀请我们去挖。
为此,我们自行组织了一个挖鼠队,队长由王肇旺担任。西面挖到花家荡,南面挖到嘶马。
我们在花荡时,听说村里又先后成立了两个挖老鼠队,要与我们挥锹共舞。其中一队,出师不利,老鼠没挖到,倒有一人先丢了一条刚做的新裤。那时布票很紧张,几个人的布票合在一起才能做一条新衣。另一队战局如何,一无所知。此话暂且不表。
就我们在花荡而言,每当中午时分,太阳晒得大地发烫,我们还在挖陷阱,来回奔跑巡检,一刻不停。嘴里干得舌头都拉不动,肚里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取出干饼,全身浸泡在河里,将头露在水面,咬一口干饼,喝一口河水,既降温消暑,又饱肚提神,实在是“可口可乐”!
那时,每当太阳西下铲土,我们就担挑死老鼠进村。某日,光我弟兄二人,挖的老鼠就有170多只,是我们出征以来最多的一次。生产队要付出原粮(没有去皮的粮食)三十多斤,钱要付八九块。全队算下来要付出百十多斤原粮,钱要付出几十块。会计一脸无奈,队长一想说:“一毛屎坑的死老鼠活着一天要吃多少粮,作撅多少地?!这点粮钱算不了什么!”可对我们而言,却是一笔大收入!那时生产队做一天工才几毛钱。人们的口粮一天才几两原粮。难怪我们的“老鼠队长”高傲地说“我比教授还强!”
花家荡挖老鼠是我们西去的最后一村。此后,我们应约转头南向。
在苍松挖老鼠时,我们约定,不再将死老鼠揹回计数,而是以老鼠尾巴计数。既减少了我们的麻烦,也避免了他们见到成堆的老鼠会作呕。
我们晚上吃在那里,睡在那里。吃的是扎嗓面。睡的是望天床。所谓扎嗓面,是我们将生产队酬勤的大麦,自已当晚推磨成的面,连皮带壳一起下锅煮成的糊糊。芒刺虽然扎喉咙也得喝。所谓望天床,就是将从生产队借来的门板放在空旷的地上,一头垫上几块砖头,对着星星,喂着蚊虫,露天里和衣而睡。
南下挖老鼠一直挖到嘶马,此时我们口袋里的钢镚直蹦跶,晚上就住进了旅社,后又乘船去安徽芜湖(船票六角)买回几十斤大米,算是全家共同享受了一场。
真是:闹鼠成粪土,良田回春光。顶日饱暑气,星月卧板床。
餐食糊糊粥,茫刺扎喉嗓。钢镚直鹏达,芜湖大米香。
时间不由人,暑假即将结束,该收拾回学校,开始另一场征程!
|